
用最专业的眼光看待互联网
立即咨询每天下午三点,龙王庙旁的老榕树下榕树下总会准时响起洗牌的哗啦声。
四张折叠小木桌拼在一起,围着八个白发苍苍的老人。坐在东首的是陈的是陈伯,退休的邮递员,一双送信四十年的手布满老茧,却异常灵巧地捻着牌。他对面是老周,前中学数学老师,鼻梁上的老花镜滑到一半,眯着眼算牌。
“老陈,今天带了多少本钱来啊?”老周推推眼镜,笑容里带着数学老师的精明。
陈伯不答,只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硬币,“叮当”一声放在桌上。这不是真钱,是他们这群老人的规矩——每人都用同样数量的硬币做筹码,输光的人第二天要请大家喝早茶。
“少废话,出牌。”陈伯甩出两张红桃。
这是他们的他们的日常,风雨无阻。老榕树冠如巨伞,投下一片阴凉,树根盘虬处还放着几个旧热水瓶和搪瓷杯。老人们在这里打了十几年扑克,从黑发打到白头。
今天的牌局进行到第四轮,陈伯已经连输三把。他眉头紧锁,手里的牌捏得死紧。
“老陈今天心不在焉啊,”旁边观战的老李嗑着瓜子,“是不是你家那小孙子又来要钱买什么游戏机了?”
陈伯哼了一声,不置可否。他确实有心事——儿子昨天又提了接他去省城同住的事。
牌过三巡,陈伯摸到了一手绝佳的好牌:双王,四个2,一把顺子。他心里一跳,这样的牌面一年也难得见一次。
老周似乎看出了什么,悠悠地说:“好牌要好好打,烂牌更要仔细打。人生如牌局,不在于抓到什么牌,而在于怎么打。”
陈伯正要出牌,手机突然响了。他掏出一部老人机,眯眼看了一会儿,才笨拙地按下接听键。
“爸,考虑,考虑得怎么样了?下个月我就回去接你。”儿子的声音大得全桌都听得见。
陈伯支吾几句挂了电话,再低头看牌时,刚才那股必胜的气势已经泄了一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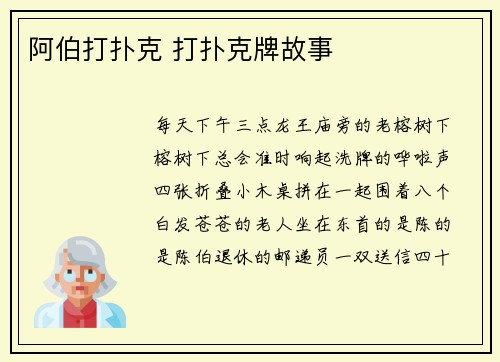
“儿子要接你去享福啊?”老周问。
“嗯。”陈伯闷闷地应了一声。
“好事啊!以后就不用在这跟我们这些老头子混了。”老李笑道。
陈伯没说话,只打出一对2。牌局继续,但他的心思明显已经不在了。
几轮下来,尽管牌面极佳,陈伯却打得犹豫不决,错失良机。老周以一个巧妙的小三带一结束了牌局。
“怎么可能?”观战的人都凑过来看陈伯的牌,“这么好的牌都能输?”
陈伯苦笑,把剩下的牌扔在桌上:“心思不在,好牌也打不好。”
老周慢慢收着牌,说:“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群老家伙天天来这里打牌吗?”
陈伯摇头。
微扑克“不是为了赢这几个硬币,”老周指指桌上的筹码,“是为了还有人愿意跟我们争个输赢。”
一句话说得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老周继续说:“我女儿也接我去住过三个月。一百二十平的大房子,白天就我一个人。智能电视不会开,燃气灶不敢碰,下楼怕迷路。坐在阳台上,连个吵架的人都没有。”
“是啊,”老李接话,“我去年在儿子那儿住了半年,差点没憋出病来。回来那天,提着行李直接来了这儿,看见你们已经在打牌,就像从来没离开过一样。”
陈伯摩挲着手中的旧扑克,牌角已经磨得发白。这副牌跟了他们五年,见证了多少午后时光。
“可是一个人住,你们不觉得孤单吗?”他问。
“孤单?”老周笑了,指着这榕树下的方寸之地,“这里有八个人陪你聊天、斗嘴、打牌,哪来的孤单?倒是去了子女家,那才是真孤单。”
夕阳西斜,金光透过榕树叶隙洒在桌上。今天的牌局接近尾声,大家开始数各自的硬币。
“明天该谁请早茶了?”有人问。
“老陈输了最多,按理说他请。不过他要走了,就算了吧。”
陈伯突然站起来:“谁说要走了?我哪儿也不去。”
大家都惊讶地看着他。
“可是你儿子那边...”
“我会跟他说,这里有人天天等着赢我的钱,我走不开。”陈伯笑得狡黠,“再说,我今天输这么多,不得翻本吗?”
众人大笑,各自收拾桌椅。老周悄悄把几个硬币塞回陈伯兜里:“留着明天翻本。”
第二天下午三点,陈伯准时出现在榕树下,手里还拎着一副新扑克。
“来来来,今天必须把老周打得认输!”
老周慢条斯理地坐下,洗牌的手法娴熟如魔术师:“就凭你?”
洗牌声响起,如同往日,如同往后无数个下午。
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,城市日新月异,而榕树下的这一方小天地,却仿佛被时光遗忘。八位老人,几副扑克,编织出一个抵御孤独与遗忘的江湖。
陈伯知道,有一天他们会一个个离开这个牌桌,但只要还有两个人坐在这里,哗啦啦的洗牌声就会继续响起,像一个无声的誓言:我们拒绝被边缘化,我们还在生活中央,我们还渴望输赢。
这就是阿伯们的扑克江湖——没有赌注,却押上了全部尊严;看似消磨时间,实则是在与时间抗争。